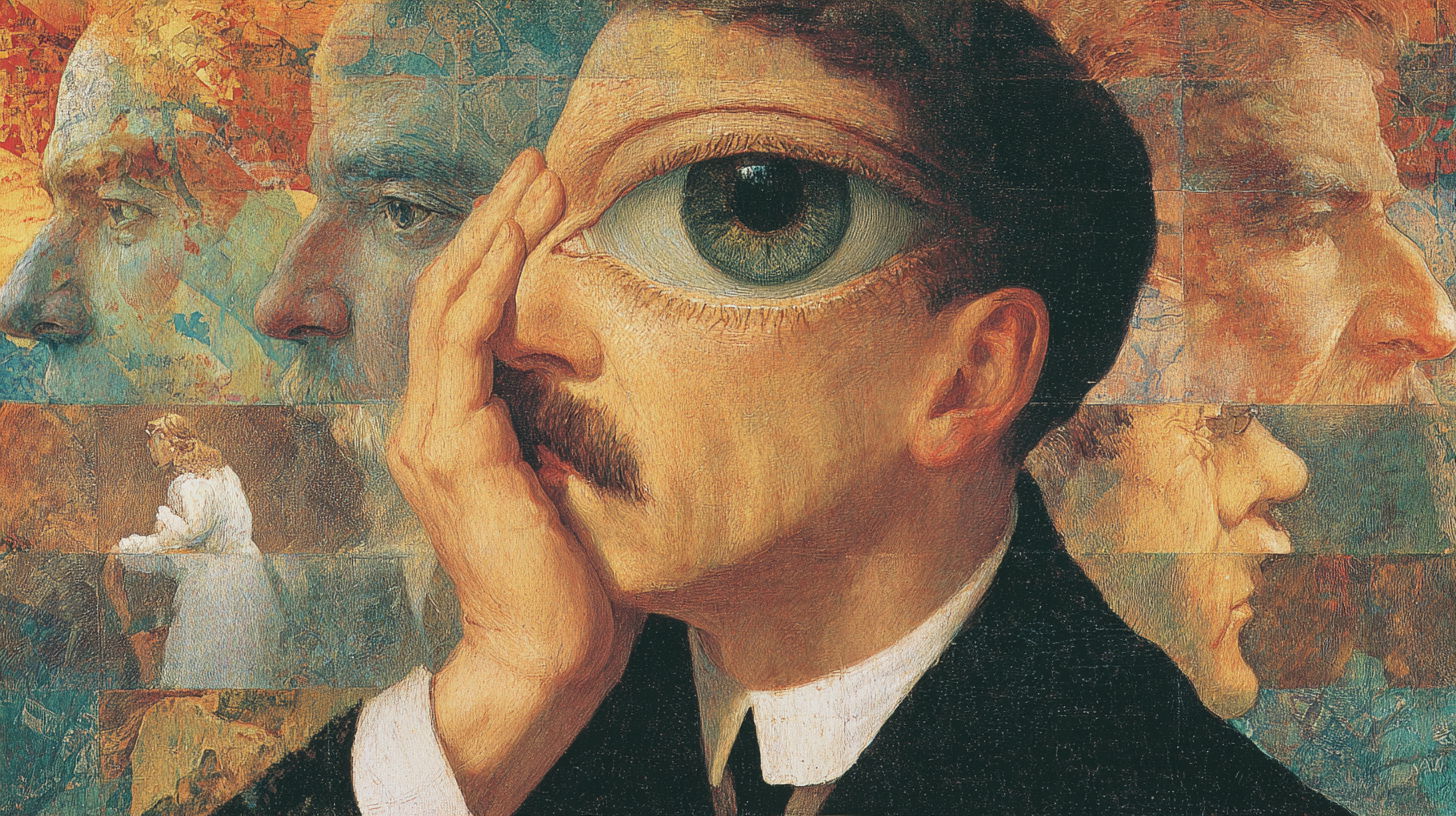“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相对于“仁”这样具有结论色彩、标的性质的概念,“诚”更具有方法和路径的意义。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为何并非遥不可及?我以为关键反而在诚。
宰我问三年之丧,以为三年太长,一年足矣,孔子的回答是“心安则为之”。何以知心安不安,关键仍在诚,否则的话,明明心不安却要说自己安,正像这一则里宰我所做的那样,就会因为不诚而不安,即使口舌上赢了,心里面的冲突却会激化。所以孔子后来说“宰我不仁”,这当然不是说宰我是个坏人,而是说他这样口是心非,就远离了仁。
这里有四个问题。
1. 孔子如何知道宰我真的心不安?
这个问题在西方哲学的领域,就是著名的“他心问题”。孔子其实对此也做了回答: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的这个回答好就好在孔子不是说谁规定了三年之丧,这个人是如何权威,我们就得照做——这恰恰是很多迷惘的现代人在争辩中经常做的——孔子是从孩子出生三年之后才能离开父母怀抱这样的人生发展规律来说。这样一来,孝,和守丧之礼就具有了一种类似集体本能的意义。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最大贡献就是为周礼这种外在于人的礼仪系统,赋予了人在进化中产生的一种共通的内在心理根源。当然你可以否认这种心理根源是共有的,孔子当然也不知道什么他心问题,想必他也无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一旦你承认这种心理根源存在,就要面对诚的问题。
2. 诚有什么用?
《中庸》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基本解释了诚的作用,诚则明,这个明可类比于现象学的明见性,根据意向性,意识总要有意识对象,那个被意识到的对象是明见的,确凿无疑。所以诚的作用是可以面对内心真实的想法。当你真切地知道内心里的想法,你的行为就不会和这种内心的需要相违背,否则你就是在防御。防御,是作为军事迷的弗洛伊德刻意挑选的一个词,并不特别好理解,这里有文化的差异。但如果换作具有中国色彩的“不诚”,就很好理解了。这一点和精神分析对治疗路径假设联系起来,“潜意识意识化”就是说将你没有意识到的内心真实的想法带入意识之中。经典的精神分析是不强调行为干预的,在经过潜意识意识化之后,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选择。而一旦你意识到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如果你还不行动,那么只能说明你的防御还在,或者你其实还没有真的意识到那些被你压抑的潜意识。这其实和知行合一的道理是一致的。你知道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原因其实不在行动方面,而是你其实并不真的知道那些道理,你只是以为你知道,反过来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就一定可以行动,不用任何人劝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并不仅仅在说学习的态度,这句话的关键还在那个诚字。
3. 看起来诚意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善,人们或许也可以诚心去做恶。
这个问题,我以为在孔子那里不是一个问题,对周礼,孔子认为它的基础在人心。从进化的角度,这也是合理的,如果一个物种总是诚心正意地去做恶,那么这个物种恐怕早就在自相残杀中灭亡了。所以孟子才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好的,尽管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不去选择依照本心去做,继而骗自己我做的就是出自本心,就是一件好事,这使得一个人或许能够毫无愧疚地去做坏事,但是他至少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坏的。所以才说人人皆有良知,良知就是不虑而知的那些知。就是如恶恶臭,好好色一般本能性的东西。
4. 既然人人皆有良知,为什么世间会有恶行?
这个问题就要先要辨析本善的问题。孔子从未说过性本善的话,孟子说过性善,但是没说过性本善,差一副词,差很远。《中庸》上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又说:择善固执。如果人性本善,那么率性而为就足够了,后面根本不需要修道,不需要教化;如果人性本善,何以还需要择善?何以还需要固执地去坚持?所以人性本善其实在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的体系里有着不可化解的逻辑矛盾。由此可推知,孟子的良知,以致“四端”,都不是本善的概念,而只是对善的一种趋向,至多是不虑而知善,向善,意即人们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才是好的,或者说人心向好,人心向善。这样的解释,使得我们不再面临人性本善所将要面对的逻辑难题和明显悖谬的经验事实,同时也为恶行的出现提供了解释空间:毕竟,知善向善而不能为善甚至转而为恶的人简直不要太多。罗杰斯依照人本主义的治疗假设在学校教育中进行的实验之所以失败,也可能和他关于人性本善的基本假设有关。
由此,经典精神分析对于心理问题的冲突 - 防御的假设,与儒家关于不诚而心不安的理解就找到了一个共通点。如何激发来访关于“诚”的追求,如何让来访面对一个真实的自己,也可能成为中国古典思想提供给心理治疗的一种思想资源。